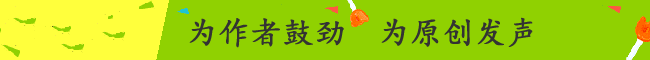母亲进城来
九十年代中期,我请母亲来广州帮我带孩子,也想趁机把她接到身边来尽尽孝心,让她在城里享受与乡村不一样的幸福和快乐。
母亲到广州那天,我不知出门张望了多少回。大老远,一看到侄儿扶着母亲下车,我便急忙迎上去,母亲气色很好,也显得异常地开心,崭新的衣衫,带着一条乡村流行的蓝色头巾,看得出母亲来时精心收拾了自己。一见到我,她便对我说:“九满啊!我昨晚激动得一夜没睡,天蒙蒙亮时才睡着。”我连忙搀起母亲那瘦弱的臂膀。
初来乍到,母亲对一切都感到新鲜,兴奋得像个孩子。我为了证明自己可以让母亲在这里过得很舒心,把她的一日三餐,还有日常起居都一一作了规划。比如为了方便母亲起夜,我特意在她的床头放置了一盏台灯。我想,母亲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吃好,还需要一份惬意又舒适的生活环境。
那时候,我时常出差。出门在外,看到母亲喜欢吃的食物,便想着回广州时带一些。出差回来,每餐都会加菜,做的都是母亲喜欢吃的。吃着我做的饭菜,母亲的心里荡起美满的波纹。她曾对我说:“九满,你在家的时候,从没拈过厨房,没想到你做的饭菜,这么精致!这么可口!”我听着母亲的赞誉,一种幸福感在心里荡漾。我们边吃边聊,空气中氤氲了满满的香暖的味道。母亲胃口好,从来不对饭菜挑咸拣淡,每顿吃的都津津有味。我喜欢看母亲吃饭,也喜欢变着花样给母亲做菜,被母亲需要,真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。
母亲来到我们家后,我和妻子感觉心里有了依靠,特别踏实,特别温暖。而且,我随时都可以叫“妈”,听着母亲的应答声,满足、心安!每次回家,远远的,我都能看到母亲站在阳台上等着我回家的身影,那影子小小的、瘦瘦的,有些慈祥,有些亲切。走到家门口,刚从衣袋里掏出钥匙,门就从里面开了,母亲笑眯眯地站着,脸上密密的褶子又恢复了生动,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快要融化在家的温馨中,融化在母亲深深的爱里了。
母亲喜欢看电视,看到粤剧,她感觉有点湖南花鼓戏的韵味,她会长时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,旁若无人般沉浸在剧情里。在家的日子,我会尽量多抽些时间陪母亲聊天,任由一阵阵温情在心头翻涌,我也能感受到母亲的满足,我也能感觉到母亲到我们家来,真的很高兴,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我的童年、少年时的往事,她叹息,我落泪,我的妻子像听童话故事般地入神。我和母亲相处,既是母子,又像朋友,我总是把自己的心事说给她听,然后她就会帮我分析、解难。有时太晚了,我们催母亲休息,她总说没有瞌睡。其实,母亲就是想跟我们多待一会,不想把宝贵的时间用来睡觉。
母亲对儿女的付出从不期待回报,但我还是希望能让她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。那些日子,我和妻子说给母亲买这个,母亲摇摇头,说不要;说给母亲买那个,母亲又摇摇头,说不要。母亲是怕我们花钱。后来,妻子硬是给她买回睡衣、皮鞋等个人生活用品,母亲高兴得宝贝似地捧着,满足地说:“在我们乡下买不到这么适穿又好看的物件!”听着母亲的夸奖,我既为母亲乐观而高兴,又为她容易满足而感到心疼。
母亲在我们身边的日子,她成了我们家的核心和灵魂。我女儿的活泼调皮,更是让母亲焕发了久违的快乐。母亲心细如尘,每次给我女儿洗澡,她都是反反复复地将热水冷水翻来覆去地进行调试、勾兑,直到水温适合。母亲才为我女儿极合力度地擦拭,动作是那样轻柔细微,如春风拂物,润物无声,无不传递着爱的伟大。
母亲进城不久,就找到伴了。一位与我们住在同一楼层的老人。两位老人坐在江边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虽然口音不同,聊天也不顺畅,但两位新朋友在一起一呆就是半天。有一次,母亲在那位朋友的怂恿下,把楼下饭店杀鸡遗弃的内脏带回家来,我知道后,说她不该要人家的废弃物?而且一连串地凶她。母亲难堪地怵在那儿,毫无立锥之地,她很不自在,看上去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,可怜兮兮。等我发完脾气,母亲小声说:“我不是穷怕了吗?我不是舍不得浪费吗?”我听了母亲的话,心里涌起一阵酸楚,立马就后悔了。说来,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批评母亲,也是一次让我遗憾终生的说教。
日子像念珠般,一天接着一天,从手中滑过去,串成周,串成月。在城里,母亲费心尽力地做一个好学的“学生”,她掌握了陌生的灶具、电器的使用方法,掌握了城市的生存法则,摸透了我家附近错综杂乱的街道。她像一棵从乡村移栽到城里的树,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依旧伸展着根须,汲取营养,自由而悠扬地适应着!